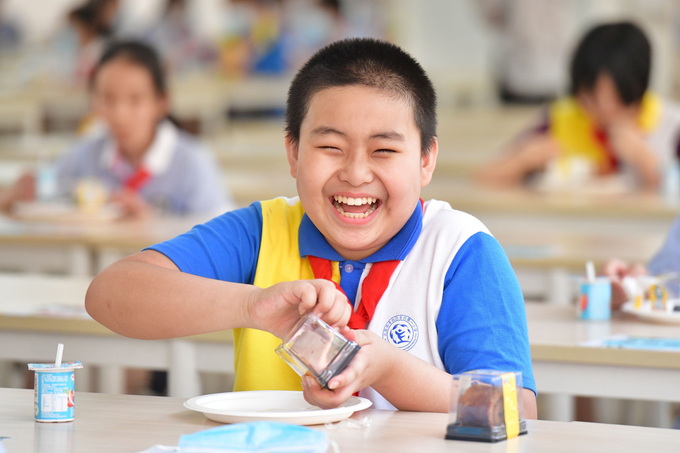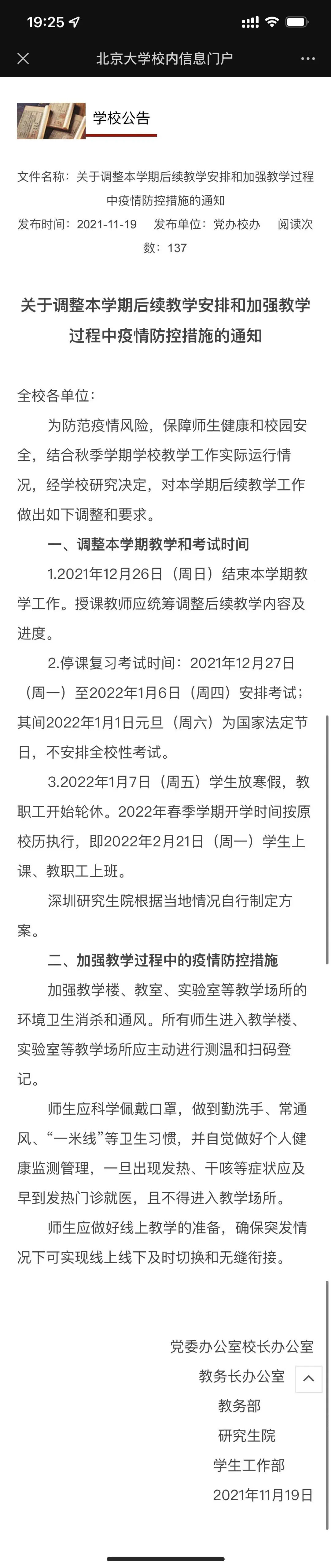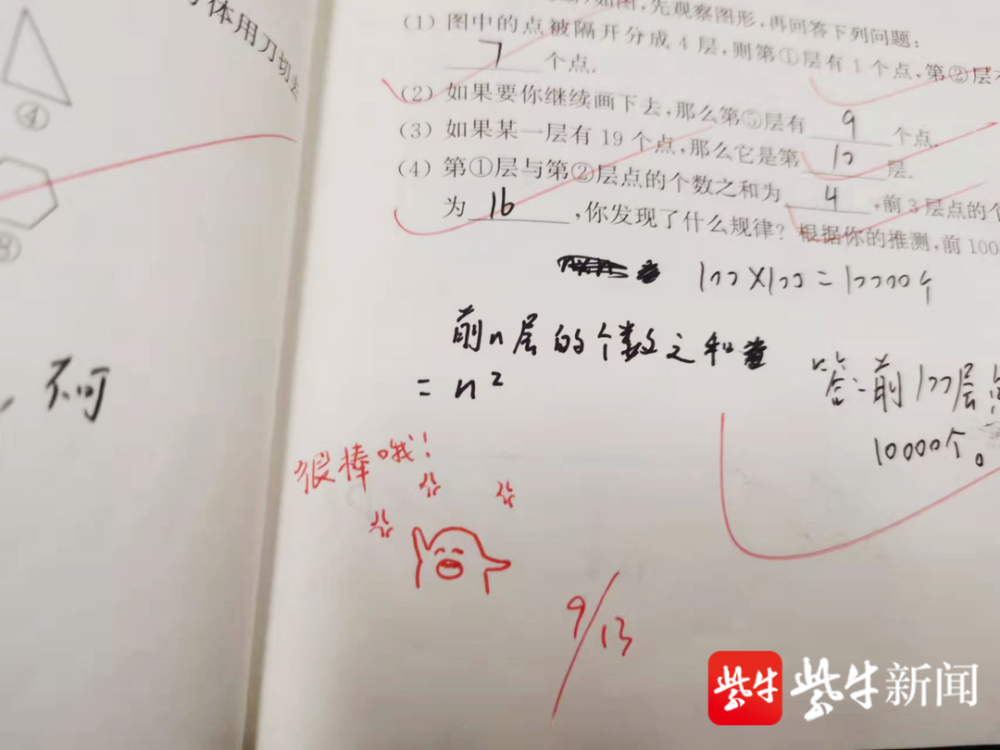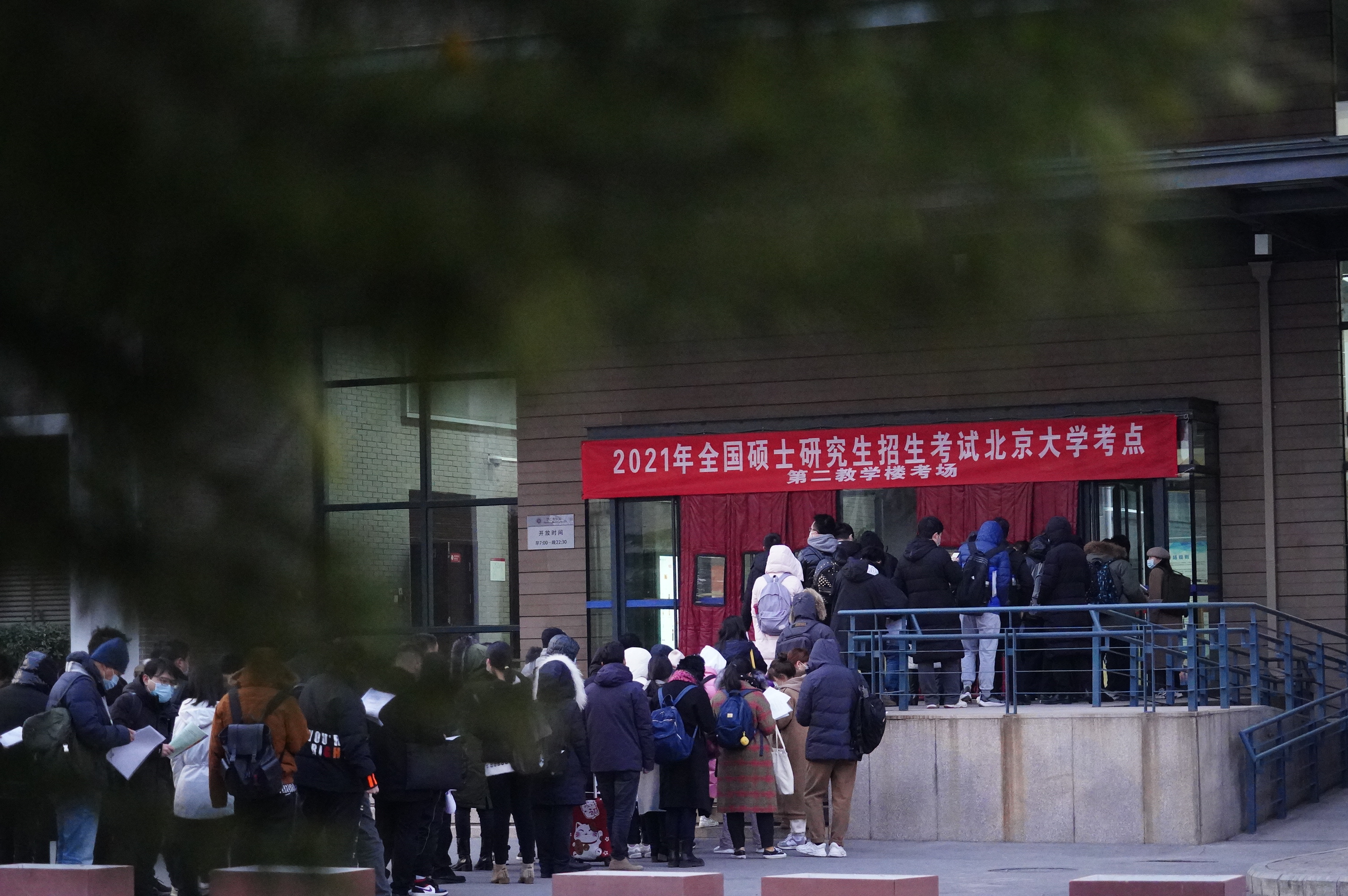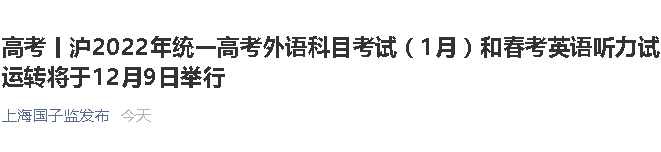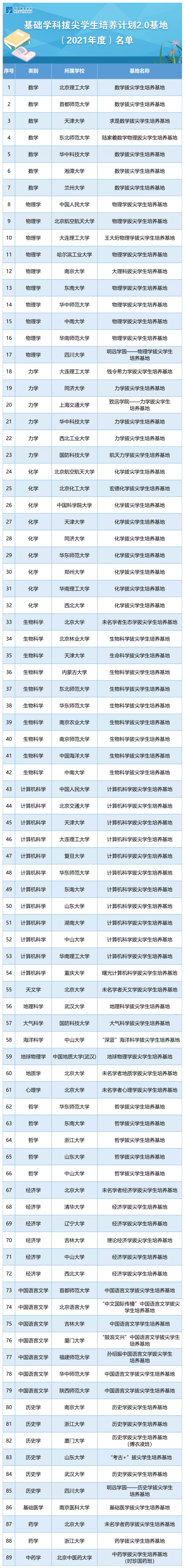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曾经指出,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的批评家,忽略或掩盖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真实文学感受。他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重要问题: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我”的隐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的兴起和对“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强调,使文学批评走进学院,进入学术生产的体系之中,得以充分的学术化和规范化。为了凸显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学术性,批评者普遍努力淡化作为批评主体的“我”,使批评看起来端庄稳重、严谨客观,却消除了批评者的性情与风格,弱化了批评的激情与锋芒。学术论文式的批评文章充满了各种理论和注释,风格却千篇一律,读起来像在听板起脸的学究高谈阔论,似乎说的并不是文学和艺术。
大量的批评者把文学作品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没有将其视为艺术品,做的是标准化的学术生产,而不是艺术鉴赏。这种批评文章在回避批评者主观感受的同时,罕见具有文学性的表达,削弱了文章的审美属性,使批评文章丧失了感染力和应有的魅力。目前存在着大量对文学批评不满的声音,与此不无关系。
文学批评不应该放弃个体审美感受
当下的文学批评,被理性的、思辨的、论证式的文字所占据。面对这种状况,人们开始怀念充满个性、满载蓬勃生命活力的率真表达。关于充满个体审美感受的文学批评,西方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西方近代以来,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批评家们主张批评脱离创作的从属地位。从狄德罗到史勒格尔,再到圣·佩韦和王尔德,纷纷坚持批评相对于创作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艺术性。
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认为,批评家同时也是艺术家,批评之于创作,有其独立性,批评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作家的意图,创作对于批评来说,是材料,就像视觉世界和情感世界是创作的材料一样,批评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他强调,文学批评应具有创造性和个性,最高层次批评的实质,是“一个人的个人灵魂的记录”。帕乌斯托夫斯基是王尔德文学批评思想的实践者,他曾写过一系列关于作家回忆片段和生活轶事的散文,结集《文学肖像》,关于王尔德的文字是其中的第一篇,足见王尔德在其心中的地位。
关于帕乌斯托夫斯基,人们更熟悉的是他出版于1955年的《金蔷薇》,在书中他总结了作家本人的创作经验,研究了许多知名作家的创作活动,探讨了创作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也是文学批评的结集。
在这本书中,他拒绝用概念框定和概括自己对文学的认知,而是用生动精妙的比喻来描述和表现艺术的现象与规律,把构思比作闪电,把灵感比作初恋,把作家喷薄而出的创作才思比作雪崩,把让人如痴如醉的情诗比作巫术。他运用生动而富有魅力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描述自己在与文学遭遇过程中真实的情感波澜与生命体验。
他评价普里什文的散文:“普里什文的语汇像盛开的花朵一般闪耀着鲜艳的光泽。它们时而像百草一般簌簌细雨,时而像清泉一般淙淙流淌,时而像小鸟一般啁啾啼啭,时而像最初的冰块那样叮当作响,最后,它们犹如星空的繁星,排成从容不迫的行列,缓缓地印入我们的脑海。”
他形容阅读亚历山大·格林作品时的感受:“猛然间,我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愁闷,郁郁地向往着灼灼生光的熏风、海水淡淡的咸味,向往着利斯,向往着它炎热的卷曲、女人似火一般的眼睛、残留着白色贝壳的黄灿灿的粗糙的岩石,以及急速地飞向湛蓝的太空的玫瑰红的云烟。”
他的评论文字是鲜活的、生动的,充满了个体生命感受。他形象地描述文学带给他心灵的抚慰与震动,表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天真和赤诚。他将老兵让·夏米从首饰作坊的尘土里筛取金子做金蔷薇的故事,比喻作家从生活的点滴中积累艺术感觉的过程;用作家穆尔塔图揭露荷兰政府和商人对爪哇人民奴役的事迹,说明作家对弘扬正义的使命。
《金蔷薇》充满了明媚绚烂的语言,神采飞扬的描写,以及感人的情节,让人忘记了这是文学批评,而认为其是美文或者小说。他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谈论文学,打破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界限,使文学批评成为艺术。
“以诗论诗”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伟大传统
事实上,中国的文学批评有着更为悠久的美文传统。精美的批评诗文下,流淌着作者丰沛的生命活力和独特的艺术感受力。
陆机的《文赋》以赋论诗文,用精致的语言和巧妙的比喻总结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以巧妙的文体形式表达精到的文学创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来概括二十四种诗歌风格和意境类型,其考究的分类和精妙的表达,让读者惊异于作者的才华。到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七言绝句的形式臧否人物,褒贬诗歌,回答了唐诗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使文学批评语言的工整、简省与精巧达到了新的高度。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对这一脉络的延伸,经过历代文人的传承,“以诗论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伟大传统。
及至现代,李健吾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他潇洒自如的美文批评风格,于社会功利目的之外,注重表达个人的阅读印象和感悟,其显著的主体意识使他的批评文字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以随和平等的话语姿态进行游离的讲述,枝蔓丛生,经常借题发挥,好似与老友闲聊,自在而从容。
比如在评论《边城》时,他用大段的文字谈论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对作者的了解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小说家与艺术家的区别等内容,似乎与文章的主题关系不大,看似闲笔,但这些内容实际是他在评价作品之前,阐述自己的批评观念,在分析和解读作品之前,让读者了解批评家。
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作品只是他表达艺术感觉的由头,他真正要向读者表现的是“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他不重逻辑分析,重视直觉感悟,用象征和比喻触发和表现印象,敏锐而机智,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感悟作品,碰撞出独特的审美经验。
比如他评价叶紫的小说:“叶紫的小说始终仿佛一棵烧焦了的幼树,没有《生死场》行文的情致,没有《一千八百担》语言的生动,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击的暮春的幼树。它所象征的,这里什么也不见,只见苦难,和苦难之余的向上的意志。”
他的批评文章有着这个时代稀缺的个体化的审美感悟,因其真实而诚恳的表达,所以具有充分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他的文章启发读者的妙悟,引导读者的阅读,像贝阿德丽采引导但丁一样,带领读者在文学的世界中漫游,只讲述印象,不妄下结论,引导读者生发属于个体的阅读感受,他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在今天依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阅读这样的文章就像阅读一篇优美的散文,在获得理论启发的同时,可以让人获得艺术的享受。
文学批评应以博观和比较来修正个体认知的偏狭
当然,这种充盈着个体审美感悟的印象式文学批评自身也存在问题。文学评论家南帆在文章《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错》中,曾对其提出过质疑:“‘学院派’的确看不上信口开河的印象主义批评。二两烧酒,一点才情,三钱想象,添加些许忧郁的表情或者泼皮般的腔调,这种配方炮制出来的文学批评不过是一些旋生旋灭的即兴之论。科学主义如此兴盛的时代,未经论证的知识不配得到足够的尊重。”南帆要说明的是,相对于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意识和历史感,印象主义所凭借的个体经验并不可靠,难能对作品进行理性的判断。
事实上,这样的担忧早就存在。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中,就列举了文学批评者在批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贵远贱近,贵古贱今;文人相轻,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学不逮文;知多偏好,人莫能圆”。即批评者主观的好恶和认知的局限对批评的有效性产生的影响。批评文章要凸显批评者个体的文学感受,又要警惕个人认知的局限影响批评的效用与公正,这看起来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但刘勰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指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需要“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即文学批评应以博观和比较来修正个体认知的偏狭。刘勰对批评者的要求在今天仍然有效。公允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建立在广泛的比较之上的,缺乏比较的批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比较意识。他在《咀华集》中指出:“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的隐秘关系。他不应当尽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以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在他看来,单纯依赖批评者自身的印象和感觉进行文学批评是不可靠的,只有与以往的杰作进行广泛而充分的比较,才能给作品准确的定位。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他实践了自己的认知。比如在讨论沈从文的作品时,他将废名和沈从文对比,指出废名的创作意在制造一种超脱的意境,而沈从文则通过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表现对美的崇拜。他又将沈从文和司汤达与乔治·桑对比,盘点沈从文创作不嗜讨论和分析,专注于诗意抒情的特点。
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品就是他评价作品的标尺,他在历代文学经典的河流中筛取与批评对象可比较的范本,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比较,印证自己的判断,他将中国古典的印象式批评和近代实证主义思想相结合,创造出极具个人风格的美文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让人追忆和回味。(张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