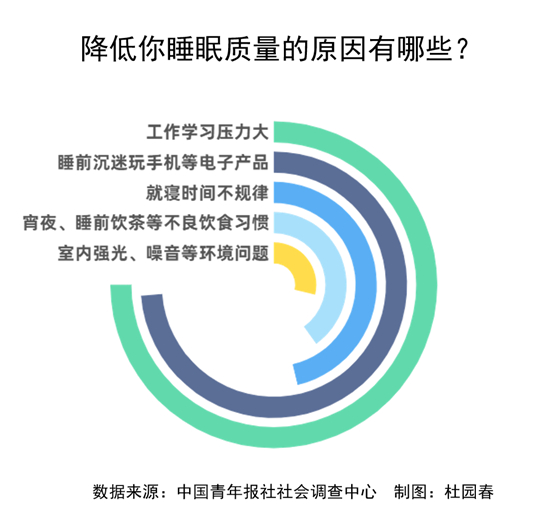“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86年曾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大量重大的新发现,近日“再惊天下”,新发现6座古蜀“祭祀坑”,已出土黄金面具等500余件重要文物。
有媒体不仅对考古现场进行直播,还连线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讲解,吸引了很多公众观看。但是,直播连线中出现的一张面孔,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他就是《盗墓笔记》系列小说的作者“南派三叔”。将严肃的考古工作与“盗墓”关联起来,许多网友对此表示不解。内蒙古大学考古文博系系主任孙璐在微博直言,这就像电影《湄公河行动》的发布会上请了以“毒枭为正面主角且杀害了缉毒警察”的小说家来谈对电影的理解一样。
此外,制片方发布的消息显示,根据《盗墓笔记》改编的动画作品《盗墓笔记秦岭神树》计划于3月24日在三星堆博物馆举办首映礼。这也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一些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发言谴责,“盗墓不等于考古”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馆方取消了这次合作。
以《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小说,更像是披着“盗墓”外衣的探险传奇:古老的传说、神秘的地域、恐怖的机关、失传的宝物……集恐怖、悬疑、推理、冒险等元素于一体,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喜爱。用南派三叔引发大家对文物的关注、热情,了解文物的价值、研究的意义,乃至用商业合作增加考古研究的投入,似乎是一件好事。但盗墓与考古水火不容,当与考古有关的新闻中出现了盗墓元素,而且还不是以负面形象示人,难免引起专业人士反感,为公众“提起考古就想到盗墓”痛心疾首。
中华民族自古就看重丧葬礼仪。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专门记载先秦礼制的《仪礼》和《礼记》中,丧礼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尊卑和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还有着一系列严密繁琐的规定。这些规定经过发展,形成了宗教、宗法与等级观念相结合的重丧礼俗。
也因此,古墓成为今人认识古代历史的一面镜子,古墓及墓葬中的随葬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墓葬形制、工艺、葬式以及随葬品的摆放方式等,虽然不像随葬品本身一样具有市场价值,却是古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为了最完整地记录下这些古代文化遗存中的信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墓时,需要按照专业的研究方法,对古墓进行科学的清理、记录、绘图后,再进行分析、比较、断代,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供研究使用,这一过程有时会持续很久。
中国古代有着“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历史上的多个时期都盛行厚葬,盗墓活动也随之产生。战国时《吕氏春秋》就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
盗墓者为了一己之欲,进入古墓窃取文物,不仅扰动随葬品和墓主遗骸,破坏原有的葬仪葬式,还会让其中蕴藏的珍贵信息归于错乱甚至流失。一些无知的盗墓者,还往往根据市场价值对墓中文物进行选择,大量不为文物贩子看中、极具科研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被他们随手毁弃。更有甚者,不惜动用炸药进行爆破,盗走文物的同时还对墓葬结构造成彻底的破坏。
这些都让考古工作者丧失了研究的立足点,用孙璐的话说,“他们难以理解考古学家在看到发掘现场一地狼藉,心痛自己‘又来晚了’的绝望心情”。
上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曾遭遇过一场“古墓浩劫”,给学术界留下永远的难题。上世纪80年代末,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四处寻找、偷偷摸摸地开始了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所谓“龙骨”,其实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其间,不断传出有人在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这些消息像风一样飞快地弥散各地,一些不法贩子闻讯而动,赶赴礼县,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而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
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盗掘古墓的行为,“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顺口溜,成了当时礼县最为流行的语言。渐渐地,盗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上。
1993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时任《甘肃日报》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采写的报道《古墓悲歌》,反映了当时猖獗的盗墓行径。文章写道:“他们背起铺盖卷,带着干粮,吃住在荒郊野外,当上盗掘古墓的专业户。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满山遍野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来回穿梭,拖着吊斗运土的人排成长队,全力以赴地盗掘古墓,奋不顾身地搜寻宝物。”仅仅6年时间,就有22条人命“赔”进古墓之中。
报道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省、市、县三级文物单位深感事态紧急,接二连三地召开文物保护会议。打击和保护多管齐下,使礼县的盗墓活动基本得以遏制,截获和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但大堡子山出土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流散到国内外,具体的数字已无法统计。仅目前出现的,就包含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
2004年,由考古专家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开始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的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最终确认了大堡子山遗址,就是秦文化历史上的第一陵区——西垂陵区。《史记》记载,秦国有两位国君葬于西垂。他们分别是秦襄公、秦文公。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多数自铭“秦公”:秦公簋、秦公壶、秦公鼎。但因为墓葬中文物的大量流失,考古工作者始终无法确认这座秦公大墓的主人。
这场上世纪90年代的“古墓浩劫”给考古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遗憾,这样的行为也于法不容。我国刑法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出现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多次盗掘、盗窃珍贵文物或者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等情形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日前,公安部披露的卫某刚案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为了盗掘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彬州市的彬塔,卫某刚曾先后4次到彬州市踩点,租下彬塔附近的一楼门面房,办理营业执照,在本地招收服务员,白天餐厅开门营业,到了晚间10点,卫某刚和同伙即从卫生间向下挖地道,朝着彬塔前进,挖掘往往至凌晨4点,挖掘的土用塑料编织袋小心地装好运出。
为了掩人耳目,卫某刚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每天凌晨仅搬出一袋挖出来的泥土弃置。最终如蚂蚁搬家似的,利用数月时间慢慢将地道打通。石棺、金棺、银棺、铜棺、鎏金棺、铜镜等珍稀文物被一一悄悄转移,经多人倒手卖出,获利2300万元。
5年间,卫某刚等人以相同的手法连续盗掘6座古塔,其中两座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案发后被公安机关追回的文物共95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5件、三级文物29件、一般文物57件。
该案已于2020年4月21日由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主犯卫某刚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当地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随着文物交易市场的活跃,文物价格水涨船高,在巨额利益的引诱下,不少蛰伏多年文物贩子又重新出山组织盗墓项目,而不少买家默许文物买卖“不问来路”的潜规则,则助长了非法文物贩卖行为,给打击文物犯罪带来挑战。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以及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等方式收藏取得的文物。
实际上,买卖文物也可能触犯刑法。我国刑法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某个古玩交易App开通了鉴定师直播鉴定的栏目,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古玩拍直播给他们鉴定,没想到成了“天天鉴刑”。鉴定师被戏称为“检察官”,一个个化身刑法老师:“这个是好东西,大概小三年。”“这把商周的青铜剑,不和你开玩笑,够死刑了。”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2017年以来,公安部会同国家文物局连续组织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侦破盗掘、盗窃、倒卖文物案件3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000余人,破获了一大批重大文物犯罪案件,让6万余件被盗掘、倒卖文物重新回归。
上述负责人称,近年来,虽然公安机关始终对文物犯罪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但是在暴利的驱使下,文物犯罪分子仍然在顶风作案,且手段日益专业化、智能化,文物犯罪已形成探、掘、盗、运、销“一条龙”的地下文物犯罪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三星堆考古发掘“再惊天下”的历史节点,馆方与盗墓小说的这次“跨界合作”就显得尤为不合适。作为文学作品,盗墓小说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描写并不必然会引起效仿,可能放在架空的时代背景下也不违法。但将犯罪行为的主体塑造成传奇、英雄人物,即使他们身上有再多的美德,即使架空了时间,对于缺乏法律知识的群体、对于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依然或多或少地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2013年山东青岛就曾有4名男子通过盗墓小说简单学了点皮毛技术,带着铁锹、绳子、桶等简单工具,到当地一处古墓实施盗墓“处女作”,被民警堵在墓穴里擒获。去年,也有8人因看盗墓题材影视剧萌生盗掘古墓的想法,相约来到重庆大足,连掘两个古墓都没偷到东西。归案后,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承担古墓修复费用4.6万余元。
因此,媒体和相关文博机构面对公众时,更应该慎之又慎。希望这场“盗墓不等于考古”的议论,能继去年“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蓉”火出圈后,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考古这条长期以来看着热坐着冷的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