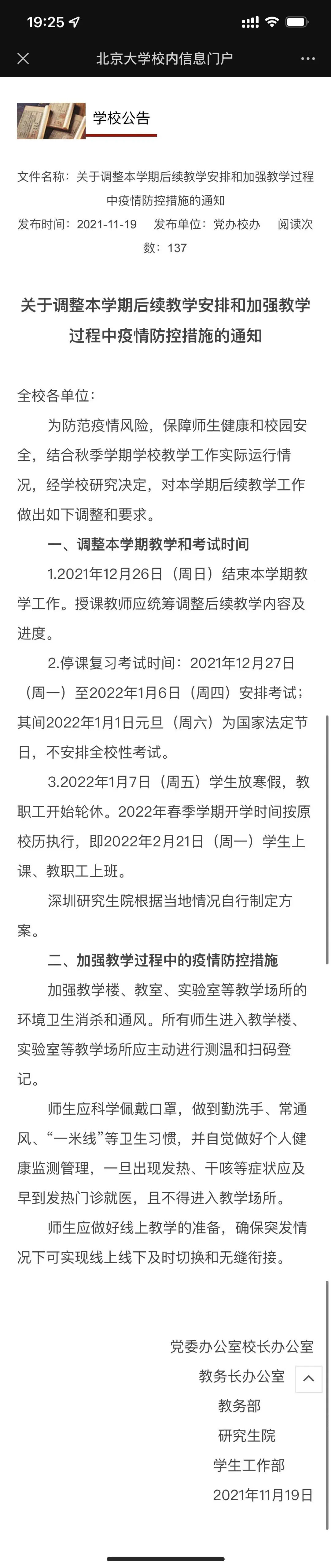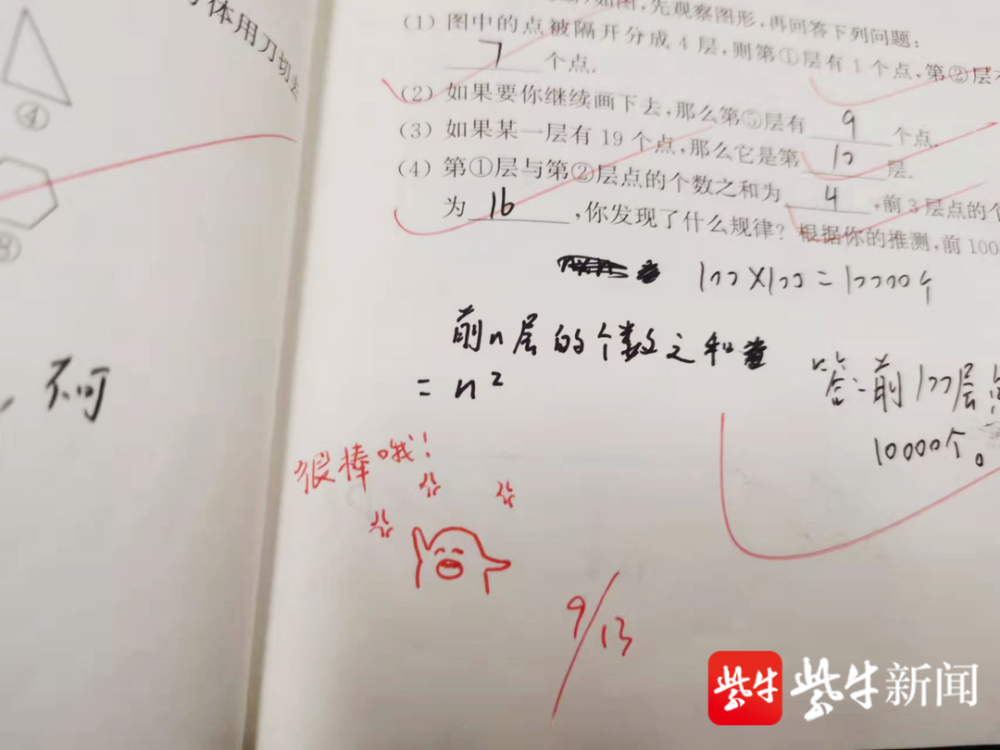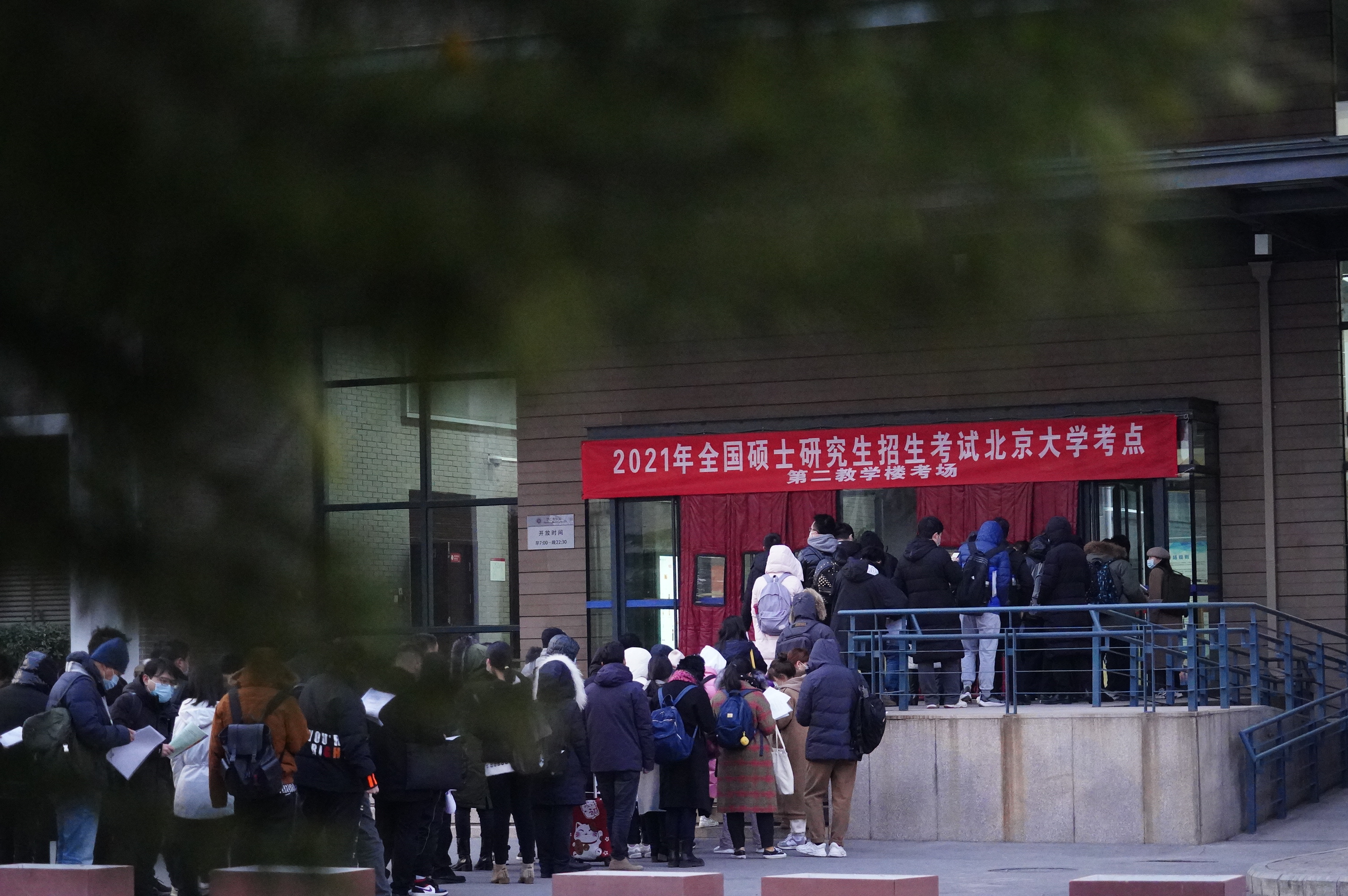第一次担任陪跑志愿者,27岁的佳瑞手腕上被系了一根蓝色的绳子,绳子长约1米,另一头的“主人”是68岁的李奶奶,她的手里紧攥着一块手帕和一根盲杖。这是她们首次“见面”,在这根陪跑绳的连接下,两个隔着辈儿的陌生人并肩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徒步。
更多人则选择跑起来。每周四和周日的早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系着陪跑绳的搭档有数十对,通常是一名陪跑志愿者搭配一位视障或听障跑者。他们大多穿着印有“黑暗跑团”的白色或橙色T恤,T恤背面的“陪跑”、“视障”、“听障”字样表明了各自的身份。
“鼓励并帮助视障、听障人群走出家门。”据黑暗跑团北京站负责人贺小云介绍,作为公益组织,黑暗跑团在平日举办例行活动强身健体,为残障跑者寻找合适的陪跑员,参与全国范围乃至国际级别的马拉松等赛事,通过帮助残障人群平等地参与大众体育活动,为他们建立起融入社会的桥梁。
让赛道公平而包容
紫色碎花雪纺老人衫和黑色布鞋,和其他视障跑友相比,李奶奶的“装备”透露了她并非资深跑者,但于她而言,这是初步却勇敢的尝试。毕竟在此之前,除了偶尔去电影院听听电影,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度过,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好多次我在外面迷路了,只能打电话让家里人来找我,后来就不爱出去了。”
“我们跑团中,有很多像李奶奶一样年纪较大的视障或听障跑者,由于不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出门没有导航,几乎很少出门跟外界接触,一部分人是在盲友的介绍下来到跑团的。”贺小云表示,于他们而言,走出家门,不与社会脱节,这样的需求和锻炼身体一样重要。
但一开始,“走出来”并非易事,贺小云曾见过一位比普通女孩皮肤白皙很多的男性盲友,“一眼就能看出他很少出门”,事实的确如此,“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出去能干什么。”因此,当跑团成长为一个能承载他们需求的固定平台后,志愿者就得成为他们勇气的守护者。
据贺小云介绍,黑暗跑团北京站成立于2019年10月,截至7月9日,在志愿北京上共有328名志愿者加入跑团的服务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年龄最大的为73岁。志愿者必须遵守3个最基本的要求,“安全第一,包括帮他避让危险、躲避障碍等;残障跑友为主,要以他的配速和感受为主;同进同退,从搭档下了地铁到训练、拉伸以及最终送上地铁,志愿者都必须陪同,绝不能中途撂挑子。”
为了尽可能感同身受,志愿者在正式陪跑前,除了要上统一的培训课,还会戴着眼罩试跑一两公里,志愿者路平小时候因鞭炮误伤导致左眼视力只有0.1,“有相似体会”,但真正要在黑暗中奔跑时,依然控制不住恐惧,“感觉脚底下随时都怕踢着、怕摔着,整个人晕乎乎的。”
“我们要求志愿者的配速比盲友的配速快1分至1分半,只有在这种宽裕的情况之下,志愿者才能及时作出反应,对盲友进行有效保护。”在活动起终点处,资深志愿者大廖热情招呼着每一位志愿者和残障跑友,安排大家合影留念。“满足仪式感”后,他会按照手里的名单给残障跑友介绍事先匹配好的志愿者,“云姐每次对志愿者培训,第一句话就是要放弃自己的配速,要记住,盲友的配速就是你的配速,保障他的安全是你今天该做的事情。”
自称“语言表达不清但特喜欢说话”的大廖,2014年就来到奥森跑步,看到一些尝试跑步但姿势不太正确的视障跑者,他就上前主动帮忙纠正姿势,慢慢地就成了陪跑员,“陪跑员要充当视障跑者的眼睛,为他们避让危险,更要帮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记得,早些年有志愿者带领视障跑者一边跑一边喊:‘让开,让开’,这样‘煞有介事’的行为不仅违背赛道文明,也会让视障跑者心里不舒服。”但近几年,随着参加马拉松赛的残障跑者不断增加,很多跑友看见他们衣服上的字样和陪跑绳都会主动避让,“我们就用手势点个赞。”大廖强调,“赛道没有特殊性,对大家都是公平且包容的。”
找到每个人的闪光点
先打车再换乘两次地铁,视障跑者杨同每次来训练,单程出行时间将近一个半小时,但他很期待这里每周一次的聚会,相比在单位的拘谨,这里让他更加松弛,“参加跑团的甭管是明眼人还是盲人,大家都像一家人,每周来这儿像聚会似的。”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黑暗跑团的活动不得不暂停,家在农村的杨同忍不住想跑步,他就让母亲骑着电动三轮车,他扶着三轮车斗边缘,母亲稍微给点油,他就慢慢地从快走到慢跑,一点点地跑起来。“一开始我妈掌握不好油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总算跑起来了。”杨同说。
而黑暗跑团给予残障跑友的远不止“跑步”本身。志愿者波波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陪跑经历,在杭州马拉松赛上,他陪跑的是一位住在市郊的盲人按摩师,那是这位跑友第一次跑马拉松,一大清早就出门准备。完赛后,视障跑友告诉波波:“这块完赛奖牌好重啊,挂在脖子上有点累。”但波波告诉他:“沉是因为这是你辛辛苦苦跑下来的。”两人的泪水突然就涌了出来,“觉得太不容易了。”
同样被感染的还有视障跑友小飞,在部队服役了5年的他曾是体能达人,自打伤了眼睛后,基本告别了体育运动,生活几乎被框在几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我经常想着出去跑跑,但想着想着就回到了现实。”去年年底,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来到跑团体验了相对放肆的奔跑,此后几无缺席,“就像和朋友约好一样,约了不好意思不去。”但每次跑步,他都会在软件上记录下公里数和配速,即便往返得花3个小时只为记录5公里。
可在采访当天,由于记者无法跟上小飞和贺小云的配速,一度掉队,小飞便主动停下等待,放弃记录里程,只是笑着表示“无论是谁,同进同退”。
在黑暗跑团里,每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热,不少视障、听障跑友都参与负责文案宣传等工作,著名手语老师同时也是听障跑友的刘春达,已经教队里很多人学会了手语,他们成立的“手语角”甚至吸引了不少视障跑者学习手语。
在贺小云看来,让更多残障跑友走出门、跑起来,仍需要社会对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公园等单位给予活动场地支持,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切实的帮助,让残障群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举措,但想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得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付出,体现价值。”
贺小云提及一则打动她的故事:二战期间,一位老人家里来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孩子,孩子提出“家里很穷,没有饭吃”,老人准备了饭菜,但前提是要帮他把砖从前院搬到后院,孩子吃饱后安心离开。次日,又一个孩子来求助,老人同样准备了餐食,但条件是,得把砖从后院搬回前院。
“不要把残障跑友搞得特殊化,要搭建平台帮助他们发挥优势、展现自己,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才能在黑暗中真正去发光。”贺小云说。(梁璇 实习生 盖姣伊)